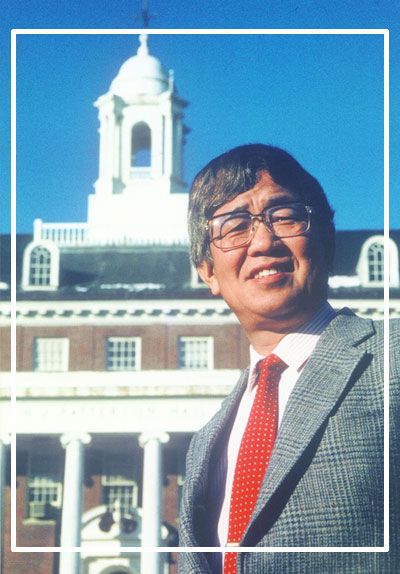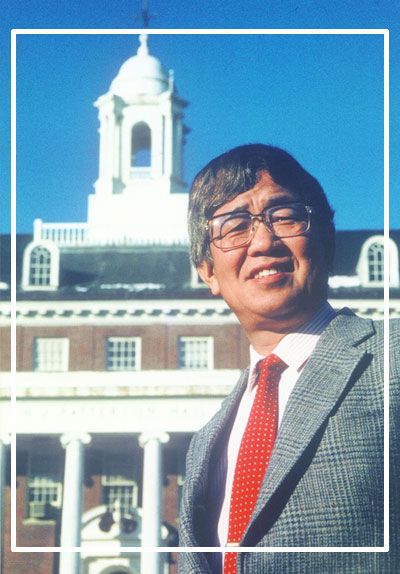
孔宪铎个人简历:
孔宪铎,1935年生于山东郯城县。是著名社会活动家、教育家,还是植物生物学和生物技术专家。台湾中兴大学学士,加
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、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。
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代理副校长,现为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山东大学等10多所学校的名誉或客座教授,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技术分校、香港科技大学、山东临沂大学的发起者和推动者。
他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起来只有两年,但最终他却取得了国外的博士学位,并先后担任过美国及香港两所大学的副校长;他已年近七旬,却重返学堂,成为北京大学一名心理学博士生,而导师整整小他30岁;像他的祖先孔子终身献身教育一样,孔家的这位第72代后人,在躬行教育的大半生中,仿佛真正感悟到了“子曰”的真谛———
子曰孔宪铎
子曰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
2500年前,孔夫子的这段人生感悟,仿佛正暗合了孔宪铎的一生。这位孔家的第72代后人,眼下正步入“从心所欲”的境界。一个月前,年近七旬的他,重返学堂,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博士生。
去年10月,北京大学人事制度的改革风波震荡海内外。此时,刚从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位置上退休的孔宪铎,被请到北京大学介绍办学经验。期间,他遇到了现任导师、北大心理学系教授王登峰。孔先生心血来潮,问:“能不能为我在哲学系安排一次讲演?我在思考‘基因与人性’方面的问题,想听听哲学家们的意见。”
当天下午,孔宪铎就登上了讲台:“为什么子女爱父母,没有父母爱子女爱得深、爱得主动?为什么三个和尚会没有水吃?这些现象是否能用基因学的知识加以解释?”
一个半小时的讲演后,听者热烈鼓掌。王登峰兴奋地走上讲台,一个劲地说:“讲得好讲得好。你就来读我的博士生吧!就研究基因与人性。”
这次偶然的讲演成为孔宪铎报考北京大学博士的初试。半年后,他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参加面试。7月,他收到录取通知书,9月,正式拜在比自己年轻30岁的王登峰门下。
在常人看来,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,但在孔宪铎看来,这丝毫没有“逾越规矩”。他经常说,年轻时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,中年时做有责任必须做的事,到了老年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更何况,孔家的祖训在先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”祖训还告诫:要“不耻下问。”
孔宪铎表示,读罢心理学博士,他将继续攻读历史学博士。
显然,孔宪铎并不缺文凭,更不缺头顶上耀眼的光环。早在30年前,他就在加拿大取得了植物学博士学位,并在美国洛杉矶大学读完了博士后。不仅如此,他还先后担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。
身材不高,满头银发,面色红润。今天,当这位曾经的大学校长,穿着颜色鲜艳的衬衫,和周围的人嘻嘻哈哈开着玩笑时,不太熟悉他的人时而会露出迟疑的神情。这时,孔校长就会一本正经反问:“难道我应该把自己打扮得老气横秋吗?”
也许,这一切都是出于对54年前那个老气横秋的少年的青春补偿。那时15岁的孔宪铎只是一个偷渡客,孤身一人在香港纱厂做小工。不要说“基因”学,他连数学都没怎么学过。因为战乱和逃亡,他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在一起,只有两年多。
有一天他病了。诊所里的人都用粤语、英语交谈,他一句也听不懂。这时,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出现了。她不仅会说英语和上海话,还懂医学术语,主动帮孔宪铎做翻译。孔宪铎第一次感到了“癞蛤蟆与天鹅的区别”。
“你无法想像那种差别给我的刺激。”事隔多年孔宪铎仍记忆犹新。从诊所出来,他就去补习班报了名。他要成为“天鹅”。为此,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‘铎’(回)也不改其乐”。
从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,苦读4年,孔宪铎参加了台湾高校在香港的招生考试,并最终迈进台中农学院(今台湾中兴大学)的门槛。但起初他丝毫找不到“天鹅”的感觉。
试题中有“H2O”,他苦思瞑想,也琢磨不出是什么意思,因他压根没学过化学。大一时化学课照开,他借了本初中化学课本恶补,但要等到同学们都睡觉了,一个人躲进厕所的小间里,关上门偷偷看。
一次,孔宪铎问一个同学:“study是什么意思?”那个同学没有立即回答,而是惊诧地望着他:“这个词你都不知道?”他没敢再问下去。
终归不是“朽木”。凭着“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”的刻苦,孔宪铎的成绩很快从最后几名升为全班第二,并一直保持到毕业。一年后,他拿着朋友们资助的学费,去加拿大攻读硕士。几年后,又拿到了博士学位。
“我到现在还不太懂微积分。”事业有成后,孔宪铎毫不掩饰,“我没学过。但我能记住公式,所以可以使用。”
1970年,孔宪铎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,转而到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博士后,在植物生化和生理学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。1974年,他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正式聘用。
第一学期结束后,有个学生找到他,试图将成绩B改成A。孔宪铎翻到他的试卷,仔细看过后,说:“不能改。你的答案就是错的。”那个学生狡辩道:“不是我的答案错,是你说的英语我根本听不懂。”
“我的英语真有那么糟糕吗?”从此,很少阅读非学术刊物的孔宪铎,开始大量阅读《读者文摘》和《花花公子》等通俗刊物,每个深夜都守在电视前看脱口秀节目,收集大量入时的笑话。
以后每次上课前,孔宪铎会先讲个笑话。学生们笑得拍桌跺脚,气喘不已。看着学生们兴奋的样子,他郑重提醒他们:无论是讲课还是讲笑话,我用的都是同一种英文。
执教3年后,孔宪铎升为副教授,又过了5年,他成为正教授,并相继在《科学》、《自然》等杂志上发表了论文。他的女儿曾抱怨,因为过于专注学术,这位学园艺出身的父亲,“把家里的花儿都养枯了”。
家里的花养枯了,但学术上的花却生机粲然。孔宪铎自豪地宣称:“在当时的植物生物学领域,我是最出色的10个人中的一位。我的学术论文,今天仍在被不断引用。”
正当孔宪铎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望时,他当年逃离的国度也开始走向世界。
一个中国学生写信给孔宪铎,说自己想出国留学,但没有钱。孔宪铎没有多想,掏出自己的钱,替他付了10所美国大学的入学申请费。虽然他们至今仍没见过面。
有位中国女学生经人介绍,辗转写信给孔宪铎,讲述自己赴美留学的愿望。她希望孔教授能借些钱给她。那笔钱不是个小数目,孔宪铎犹豫了。
“那些天我都没睡好觉,也不敢去办公室,怕看到她的信。”将近20年后,孔宪铎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行为只是出于“同情”。“其实是种责任感,是种罪恶感。数目虽然很大,但我也不是力不能及。如果我的力量允许,却不帮助她,那我……我就会有种罪恶感。”
从那时起,孔宪铎找到了自己“有责任而必须做的事”———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。
1978年,背井离乡近30年后,孔宪铎以美国大学教授的身份频繁回国。他吃惊地注意到:有1000多万人口的家乡山东临沂市,只有一所师范专科学校。
“怎么能连一所大学都没有呢?”孔宪铎为此四处奔走。
经过多年学术训练,使他对数字有超常的敏感和记忆:“北京有1200万人口,却有大学67所,而临沂一所也没有;2002年,全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%,北京、上海达到了48%以上,而临沂还不到1.7%;再看看周边的地区和国家:台湾的毛入学率是49%,韩国是52%,而美国是81%。”
孔宪铎最能打动家乡官员的一个观点是:“临沂的孩子都跑到外面去上学,谁还能回来?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,如何能发展?”他向当地政府打包票:只要你们建起大学来,我帮你们找好老师。
这呼吁一喊就是十多年。喊得许多政府官员都开始“讨厌”他。这位本来令临沂人骄傲的大教授,一度成了“坐冷板凳的人”。
直到去年秋天,临沂大学才终于奠基。孔宪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加奠基仪式。他虽兴奋但也不无遗憾:这是在临沂师专的基础上扩建的,仍然不是一所“新”大学。“我们不应为建大学而建大学,而是为了增加学习的名额,增加入学的机会。”
孔宪铎的好友、曾任临沂市副市长的綦敦祥直言相告:“不是大家不知道这个道理,但是钱呢?那可是一所大学呀!”
但孔宪铎认为这个逻辑不通:“2002年,全国在教育上的投资已占GDP的3.41%,而山东占多少呢?”他坚持认为“这不是钱的问题,而是观念的问题。现在不应该是‘科教兴国’,而应是‘国兴科教’。”
在家乡许多官员看来,孔宪铎的许多想法“不合时宜”,但当他的面,他们称之为“超前”。
3年前,孔宪铎从担任了10年的香港科大副校长位置上退休后,接受了山东建工学院名誉校长一职。在这里,他管了许多一般校长不会管的事。
学校的大门有两扇,却常常只开一边。这位名誉校长提出:为什么不都打开呢?校方答:门卫人手不够,怕不安全。“这不是理由。”他说,“不能为了自己管理的方便,而让进出的人麻烦。”两扇门都打开了,至今也没发生什么“不安全”的事。
学校里经常有人乱扔废物。孔校长找到校方,要求增加100个垃圾筒,并且要摆在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;学生反映打开水的时间太短,他立即向学校建议,早上和中午各增加半小时;甚至在世界杯比赛期间,他也要求学校一定要进行转播。
“我们办学校不是为了管学生,而应该是为学生服务。”这是孔宪铎担任近20年大学管理者的经验,“一切‘以人为本’,不能‘以管理者为本’。”
他任名誉校长期间,不仅以管琐事闻名,也常常因一些他认为很简单的事没有得到快速处理而恼火。
“我是个急性子。”孔宪铎解释道,转而又说,“在西方餐厅叫服务员时,他们答:我就来;而在中国,回答是:请等一下。这就是区别。”
相比上述所为,孔宪铎最“不合时宜”的想法,应该算是“乡村厕所改革”。
这个想法从1986年萌生。最初,他只是想推动“乡村厕所手纸运动”,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卫生纸渐渐在农村普及了,他便把目光转向了厕所改造。
一次,孔宪铎去一所镇中学参观,这是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。“教学楼很漂亮,但一进校门我就知道厕所在哪儿。”他径直进去看,觉得“不堪入目”。
“培养人格要从尊严开始,尊严从最基本的隐私保护开始。”孔宪铎说,“就算从卫生角度考虑,也应该把厕所弄得干净点儿,至少要有水冲。”
当地人说,人吃的水都紧张,哪里有水冲厕所?更何况,室外厕所,冬季冲厕会结冰。
“因为两个月可能结冰,而让其余10个月都臭烘烘的?”孔宪铎不理解。
他觉得,现在很多中国人“远虑”太多,因而失去了解决“近忧”的勇气。
“总会有办法的。”他回到香港,向朋友们募捐了约10万港币,准备选一所学校,建一个示范厕所:要有档板,有门,有冲水设备。
“一间厕所能改变什么?”有人不解地问。
孔宪铎想都没想回答道:“可以改变人的观念。可以建立人的尊严。这就是教育。”
庄子曰:道在屎溺。
孔宪铎表示,自己的一生结束后,他希望墓碑上不写博士、教授或校长之类的头衔,只写:“中国乡村厕所运动的推动者”。
相关链接1:
●要明白教育的重要,这代苦,下代就会好;一代不苦,就代代苦。其实,政府对大学生的投资,学生工作十年所交的税款就可相抵;学生若工作三十年,不是什么都赚回来了吗?教育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国家的问题,只是它不会有很快的效果。不能以办银行的观念办学校。要保障政府对教育的投资,不能靠个别官员的高瞻远瞩,不能“事在人为”,唯有依靠法制。要在宪法上规定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收入的一定比率。
在经济挂帅的情况下,教育的竞争能力相对减弱。为人父母官者,不能把对教育的投资看成一种可有可无的消费。为人父母者虽然会无条件地为孩子读书投资,却没有普及教育的经济能力,这个能力只有政府有,许多事情必须政府来做。
●中国留学政策应当让孩子们走,能走的都走!因为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很强,最终会回到祖国的。让年轻人出国游学好比在银行储蓄,利息还是你的。很多中国学生在国内没有什么特别表现,甚至过得很苦恼很困顿,但一出国,马上就很有成就了。我觉得我们教育工作者要思索了,人没有变,只是环境变了,竞争的游戏规则变了,这说明了环境之于人才成长的意义。比如,在美国学习和研究,与加拿大有显著不同,美国比较积极高效不拘一格,压力大,奖赏好。
很多时候,中国人竞争是打麻将心态,一坐下来进入比赛,所有人都是敌人。打麻将的基本原则是,你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之上。最高境界就是我知道别人会怎样和牌,而把他需要的牌扣下,不让他和。而外国的氛围有些像打桥牌,四个人中有两个是partner,是朋友,是合作者,要communication,必须联合起来协同作战。
●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还有很多课要补,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以18岁到22岁适龄学生能够进大学的,在美国是50%,日本也是50%。亚洲四小龙,除了香港以外,都是30%。香港虽然仅有18%在香港读大学,但到海外读大学的有百分之十几,加起来也在30%的样子。而大陆入学比例则太低了,这埋没了多少人才啊!
要运作大学,要让大学成为社会的明星,要让大学有更大的影响力。比如哈佛,它的经济实力高达200亿美元,拥有一大批杰出的教授,说它是“帝国”,似乎并不为过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,美国哈佛大学的经验是很好的典范:哈佛大学每年通过各种渠道筹集100多亿美元的办学经费(大约相当于1996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1671亿元的1/2)。哈佛经验对我国高校如何走出经费不足的困境是很有启示意义的。
(来源:《齐鲁周刊》)
链接2:
一进门,我称呼他孔校长,孔先生说:“我更愿意人家叫我‘孔教授’。‘President,校长’是行政职务,‘Professor,教授’才真正是我自己,我就是个老师嘛!”话语间绽放出一个老学人老教授的谦虚平和。这位六十七岁的老教授精神矍铄,满头白发下是红润的脸庞和纯真的笑容,一身轻便的格子衬衫。
孔先生此次济南之行是帮助山东建工学院搞一个“世界名人演讲”的活动,他出面联系了六位全球闻名的学者专家来济南做学术报告。一是为济南的大学生打开一扇亲见世界顶尖科研的窗子,二是为山东建工学院扩大影响,增加知名度。而且,学生们会因此对自己的学校产生自豪感,对自己更有信。
流亡童年和纱厂小工
孔先生把自己的通达和今天的成就归功于早年的颠沛流离,“很多品格是要从苦难中淬砺而出的。”
1935年,他出生于山东临沂郯城的乡下,这是山东最南端。从中日战争到国内革命.战争,家乡一直都是战区。他从小就跟着家人从一个村庄逃离到另一个村庄,童年充满了贫苦、战乱、逃离和朝不保夕的恐慌。孔先生至今还对日军扫荡的情景记忆犹新:大家躲藏在高粱地里,不敢出声,远远听到日军的车马通过。他亲眼见过日军在郊外用正在田间耕作的农民当活靶练习射击。
那段日子里,他很少能在同一村庄住上一年半载;连安居下来过日子都不可能,教育对他更是奢侈的——国家战乱,大城市的高等教育尚且遭到破坏,更遑论乡间的基础教育?
十一岁那年,他和一群同乡远逃到上海,做了三年学徒工,后来又辗转偷渡到香港。在42年后,孔先生以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的身份参加时任港督卫奕信的茶叙,港督问他是怎么来香港的,孔先生说:“假使说实话,我犯法;不说实话,是犯上。”港督问为什么。孔先生说:“我是偷渡来的。”十五岁的少年来到举目无亲的香港,只有出卖苦力为生。他每天在纱厂做小工,一天要做十二个小时,扣去食宿费用,工钱就只有五毛,还曾因肺部吸入太多棉絮而咯血。
没有小学中学的大学和大学校长
1954年,孔先生来到台湾,考入台中农学院,靠奖学金念完了大学。他回首那段充满希望的青春时光:“生活很艰苦,精神上却很愉快,就像爬楼梯一样,人还在底层,但相信自己未来会爬得很高。”由于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,上大学的头一年,功课非常吃力,上化学课不知道H2O代表水,上物理不知道什么是电子。于是他夜以继日的苦读,甚至大学期间,连同宿舍的同学他也不怎么认识——因为晚上人家都回来睡觉,而他却出去开夜车温习功课。
1958年夏,孔宪铎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。这四年大学,是他第一次安安稳稳坐下来读书的四年,他第一次尝到了毕业的滋味,第一次拥有了一份毕业证书。他坦言,在自己背后有一股使他勇往直前、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力量,它来自他的同学兼女朋友、后来又成为了他的妻子的傅静珍。她对他说:“使自己有用是得到快乐的最好方法。”
几年后,他考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,先后取得硕士、博士学位,成为植物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方面的专家。1971年,孔先生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、马里兰大学做研究员和教授。后又历任系主任、副院长、副校长。
1991年,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广罗名士专家共创一流名牌大学,有人力荐孔先生做理学院院长。此时,正是孔宪铎在美国事业大发展的时期,但是有件他一直想做的事情,就是为自己的祖国出力,于是他决定前赴香港科大。1992年,他就任香港科大副校长。抵港就职那天,他被安排在维多利亚湾的会展中心楼上的豪华公寓里,他几乎一夜未眠,回想40年前偷渡来港,不禁感叹:人生如梦,只要坚持不懈、把握机遇,梦想就会成真。
当他来到香港科大就职时,主持人向学生介绍他的履历,学生们没有反应,但提到他是孔子的第七十二代后人时,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好像是一个轮回,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,他的子孙孔宪铎也在为教育奔走呼号。沿着名家的坎坷人生路,体会他的思想轨迹,怀想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创业豪情、士人格和报国之心……
矢志创办临沂大学与“乡村厕所运动”
作为孔子后人,孔先生一直为故里的高等教育奔走呼号,不遗余力地坚持创办临沂大学。孔先生讲:“我喊了十五年。从临沂喊到济南,从济南喊到北京,再从北京喊回济南,从济南喊回临沂,困难重重。很多人劝我不要搞了,我说那不行,临沂有近一千万人口,却没有一所大学,临沂的孩子要去外地读大学,有80%的不会回来,那临沂就严重地缺乏人才,就会永远贫穷!那太可怕了!”
他著文《为什么我要办临沂大学?》,提出了“要以父母之心办教育”的观点:为人父母的总是将家里的钱精打细算,先留下保障孩子教育的钱,然后才是吃穿住用。如若家境贫寒,即使省吃俭用,也要让孩子读书。父母投资教育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利益,而是要让子女得到利益,过上好的生活。孔先生动情地说:“要是我们的父母官以父母之心办教育,教育焉有不兴之理,国家焉有不兴之理?”
孔先生现在做的一件事,颇出乎一般人的意料,那就是在故乡各个乡下修建厕所,是为“乡村厕所运动”。他说:“很多人认为这不重要,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在乡下看到的厕所有的连个帘子都没有,人们就开始如厕。一个人连自己最基本的尊严都不维护的话,你还指望他去社会上做什么大事情呢?”
采访的最后,孔先生如此简单而淡然地总结自己:“我这一辈子都在‘改良’——改良植物,改良大学,更改良人生。”
(责任编辑:linyidazhong)